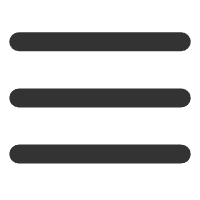读《潜规则》有感
这个假期我阅读了吴思的《潜规则》, “潜规则”这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对中国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在阅读之前,我对“潜规则”的理解是一种隐秘的、不公平的、由少数社会上层或者说是掌握权力的人制定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而受到这种规则约束或迫害的都是大部分的没有权力的人。而读了吴思先生的书后,我对“潜规则”有了更确切,更深人的理解。
“潜规则”这一概念的创始人就是吴思,而这词如今已是个非常流行的词。这本书篇幅不长,共有两个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了四个小部分:身怀利器、第二等公平、正义的边界总要老和晏氏转型;第二大部分包括了有关潜规则的定义、我们的人格理想、古今中外的假货和吴思的专访 。
在“身怀利器”中,吴思首先引用了张居正的话:“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吴思先生引用了好几个明朝故事来阐述了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官吏以权谋私,可随意地决定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如美国对伊拉克,美国有不少强兵利器,可随意发动战争。这应了一句古语“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就因为实力悬殊,所以强者特别爱打并以此来获取利益。而合法伤害权则在监狱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如清朝文学家方苞写的《狱中杂记》和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狱》,他们的著作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悲惨事实: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司局长们,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这些钱财。而在最后,吴思指出了官员受贿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只要你手中有了权,贿赂的人就会通过亲朋的渠道主动找上门来,叫你在绝对不好意思翻脸的情境中缴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们变成一拨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在“第二等公平”中,吴思就提出了公平是有等级的。第一等公平就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然而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而第二等公平就是官府强加的,却得到老百姓的广泛认可的公平。吴先生提了个很贴切的比喻, 就是现代的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很多年前,人们要交五千块的电话初装费,吴思以为这很公平, 所以称为第一等公平。但是电话公司收了钱还要拖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安装。上门了还要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或至少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他也愿意掏,只要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他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他买他们的电话机,他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所谓的第二等公平。
在“政治的边界总要老”中,吴思举了明朝大官海瑞严惩贪官污吏的例子和其他三个例子说明了中国历代惩治贪官的刑罚总是从严厉到宽松,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国家干部领取的工资,号称是皇家发的俸禄,最终来源于百姓。国家干部办公,可以看作为皇帝服务,也可以看作拿百姓的钱为百姓干活。奈何这些干部光拿钱不好好干活,还要贪赃枉法,这既侵犯了百姓的疆界,也侵犯了皇权的疆界。海瑞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吞蚕食,结果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边界两边较量了数千年,进退生死,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复着。
再到“晏氏转型”, 吴思引用了《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却被齐景公责备;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就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却被齐景公嘉许;晏子受到嘉许后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中的故事。初期时齐景公认为晏子管理不善是因为听到了身边耳目对晏子的诋毁,原因在于晏子将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作为信息通道的把关人,他们在晏子面前碰壁,预期中的利益未能实现,积攒了满腔怨恨,自然不肯传达有利于晏子的好话,也不肯拦截诋毁晏子的坏话。后期晏子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齐景公左右的人了,他们自然大说好话。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叫做晏氏转型。从一个好官向贪官过渡,有很多原因,上边和下边的压力恐怕就是最大的原因。一开始如果你是个廉洁的清官,不受贿赂,但是上边的想你向他献媚,或诱惑或威逼,而下边则想帮你欺负老百姓。这时如果你的意志不坚定,怕丢饭碗白牺牲,不敢对抗,就会坦然地欺下媚上。所以说晏氏转型可谓是一种官场生存策略的转型。
关于潜规则的定义,吴思认为是一种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这种约束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但一旦越界,必将招致报复。这种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是隐蔽的,然而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他强调潜规则涉及的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当交易双方以隐秘方式进行交易时,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
吴思这一本篇幅不长的书生动地揭露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潜规则现象,这些规则使到掌权的人获得巨大的利益,献媚贿赂的人不当得利,普通的老百姓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即使在倡导等价交换,公民人格的现代社会,潜规则还是无处不在地渗入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在我们的身边重演。在消费领域就有些不成文又心照不宣的规矩,如吃饭不能自带酒水,使用消毒碗筷、毛巾要另外付费等等。而食品行业方面,三聚氰胺,蒙牛OMP、广州瘦肉精,都是业内只做不说的公开秘密,因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必须考虑的就是如何投机取巧、吃仨混俩、偷工减料、蒙混过关,没有哪个行业是例外,甚至没有哪个人是例外,区别只是程度不同。撇开这些,就拿与我们学生息息相关来说,上一年央视曝光了八大“教育潜规则”,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这些潜规则包括“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择校费“被自愿”、奥数改头换面、升学率还在争第一、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等。再近一点,学生当干部,找工作,老师评职称等等都有很多的潜规则,就连全国高校的排行榜都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的事。另一方面,对比西方社会,中国人更注重的是关系,有关系就是好办事,倘若家中没有当官的,没有掌权的,你可以找亲朋戚友,你可以把钱送上,自然有人为你铺路牵线。这种关系何尝不是一种潜规则。
潜规则为什么存在?吴思认为它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结构的方式。无非是有那么一拨人掌握了合法伤害权,欺负另外一边,而另外一边反抗成本太高,那我只有认账了——行,就按你说的来吧,多交点儿就多交点儿,多上点贡就上点贡。按照他的观点, 潜规则的面积扩张或者是缩小,是博弈双方的对抗问题。只有老百姓有权了,力量壮大了,潜规则这种现象才会有消失的可能。所以解决潜规则问题,就必须实行民主治国的方针,加大老百姓的民主权利;严惩贪官污吏,加强完善各行各业的监管体系,完善法律体系,从法律上保障老百姓的合法利益,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申诉权等。
潜规则在数十年内不会消失,但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进一步实现而渐渐萎缩。
2008级研究生
罗倩茗